内容详情
在故纸堆里,打响没有硝烟的战争
——读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
■孤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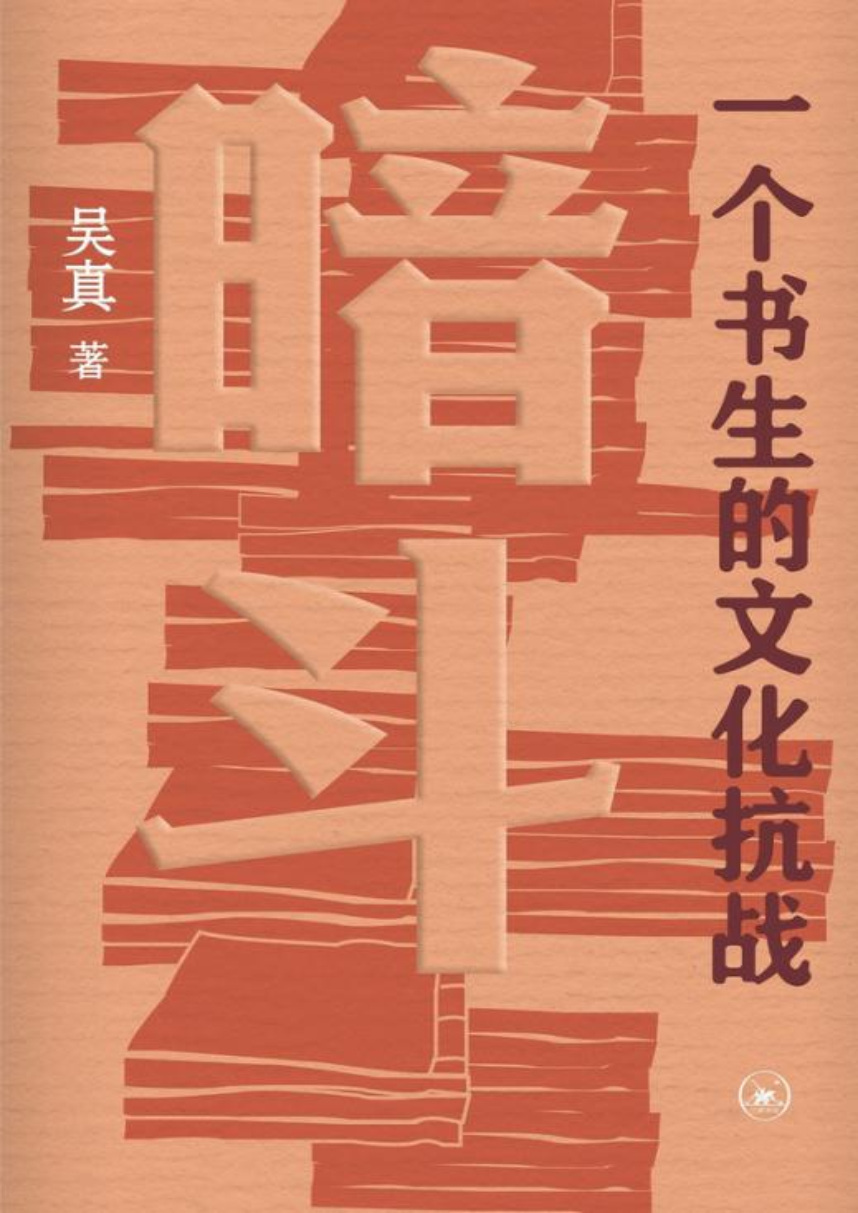
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
吴真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刚拿到吴真这本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时,感觉沉甸甸的。翻开内页,密密麻麻的脚注和文献引用,让人觉得像本严谨的学术专著,我甚至做好了要正襟危坐阅读的准备。但没翻几页,这种印象就被彻底颠覆了——它更像一部悬念迭起的非虚构作品,主角是一位看似与“抗战”二字毫不搭边的文人——郑振铎。这位五四运动的宿将、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,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,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费解的决定——他不走!
这本书细致地还原了1937年上海沦陷后,郑振铎为何选择留下,以及他如何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,进行一场孤独而决绝的“文化抗战”。当炮火摧毁城市,难民流离失所,大多数人的关切集中在血肉存亡时,郑振铎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战火中飘零的古籍。在许多人看来,这简直是“不识时务”。
但郑振铎看到了更远处。他有一段痛彻心扉的话,大致意思是,房屋工厂被毁,可以重建,甚至建得更好;但文物古籍一旦被毁或流散海外,便如人死不能复生,是一个民族无法弥补的永恒伤痕。他立志“从劫灰里救全它,从敌人手里夺下它”,并将此视作自己留守“孤岛”的“自我救赎”。这种清醒的、超越时代的文明视野,让他背负着“躲藏在上海”的道德负罪感,又毅然扛起了“万一失败则成千古罪人”的历史重担。
吴真的笔触,并未将郑振铎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悲情英雄。相反,书中充满了生活细节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宏大使命下挣扎的、真实的个人。1939年的日记里,郑振铎一边为筹措书款绞尽脑汁,甚至抵押自家藏书,一边又不断自责“购书之癖,是一大病”;他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地下抗日团体的秘密聚餐,交流情报,策划行动,一边又和妻子沉溺于麻将至深夜,并在输钱后懊恼地写下“戏无益”的忏悔。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耗与人性弱点,让他显得格外可信、可亲。他的抗战,不是在聚光灯下的慷慨激昂,而是在柴米油盐、家庭争吵、内心挣扎的日常琐碎中,一点一滴地坚持。
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,在于揭示了这场“文化暗斗”的复杂与凶险。郑振铎的战场,是上海错综复杂的古旧书业网络。吴真通过钩沉大量日记、信件、档案,尤其是引入日方史料进行对照,让我们看到,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文物收购。它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,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谋战。
书中详细描写了郑振铎为国家抢购国宝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的“局中局”。原本看似单纯的古籍买卖,背后却牵涉书商、中间人、收藏家等多方势力的博弈与抬价。更危险的是,日本军方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,每一个师团都配有“兵要地志资料班”,随军还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。日本学者如高仓正三、长泽规矩也,也一直密切注视着郑振铎的动向。他身处“虎窟之旁”,其行动、研究和藏书,始终被日本军界、情报界和学术界“围猎”。他自述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,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,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”,这绝非夸张。
正是在这种高压下,郑振铎展现了他除了书生本色外的另一面:惊人的情商、智商与胆识。他游刃于旧书业的“俗情世态”之间,善用中间人,与书林高手角力,巧妙地与各方势力周旋。在为国家抢救文献的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工作中,他凭借在上海文化商业网络中的深厚根基,与张寿镛、何炳松等人一起,争分夺秒地从日本人和北平书商手中“抢”回大批江南珍籍。最终,他们成功为国家搜购宋元善本、明清精粹一万五千余种,近三万册古籍。
读完最后一个章节,那个在庙弄寓所的书堆中埋头整理、在四马路书店里与书贾侃价、在秘密聚餐会上忧心忡忡的郑振铎形象,挥之不去。吴真通过“书籍史”的独特视角,让我们看到,每一本历经劫波、得以存世的古籍背后,都凝结着那个时代一群知识分子为守护文明血脉所付出的艰辛、智慧与勇气。他们的战斗没有硝烟,却同样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。


